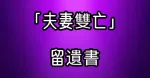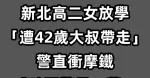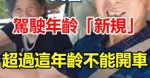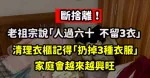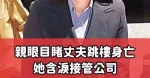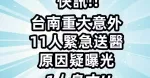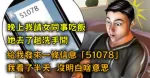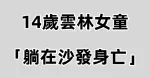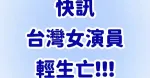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孟子發現一個規律:華夏每500年必然復興,2000年來已成現實!

2/3
從500年一復興這個天時來算,這戰國早該過去了;就說人和,也有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莊子和我孟子等無數人,也該夠了啊;可天下為何遲遲不能再度平定,到底哪裡出了問題?
大丈夫生於世間,當以平天下為志向;如果想平定這亂世,當今天下,舍我孟軻其誰?
奔波三十載,54歲高齡的孟子依舊沒有心灰意冷,並且還有著捨我其誰的勇氣。當然我們上帝視角看,孟子無疑失敗了,但我們卻不能說孟子的理想破滅了,他依舊留下了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的治世理念。
並且這句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,還在激勵著一個個後人;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而受宮刑,激勵他寫出《史記》的信念,是他覺得孔子以後500年就是他!
在這之後,華夏一有亂世,人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尋找明主。
諸葛孔明六出祁山,是將先主劉備視為明主;王猛辭桓溫而就苻堅,是覺得苻堅能平定天下;宗澤死前高呼過河!過河!岳飛風波亭高喊天日昭昭、天日昭昭,是痛恨自己未遇明主……
大略說來,夏啟家天下到商湯革命,470年而周朝建立;商湯立國到武王伐紂,又有550年;周公旦樹立周禮,到始皇帝一統華夏卻有整整800年;此後兩漢四百多年,再有魏晉南北朝大分裂;及至隋唐長期統一,已經漢末近五百年矣……
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周期規律呈現而來;幾百年大治理,就要有幾百年大分裂;這個500年的數字從孟子提出起就不精準,但趨勢卻從未改變;後來人們將這個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勢,稱為歷史周期論。
那麼這種規律背後的根源是什麼呢?四個字土地兼并!亂世之後人丁稀少,每個人都有足夠耕地,自然都是其樂融融;數百年間人口增長,加上土地兼并,沒了土地的人越來越多;當餓殍遍地之時,就是大亂之始。
但這一平一亂之間,就是上千萬人口的消逝,數百萬家庭的離散,其中多少悲傷有誰可知?
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這種重複發生的悲劇,孟子說了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,他說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這話不全是為平民說的啊!
平民看似最好欺負,但一切社稷、尊貴都是建立在無數平民基礎上的,沒有人就沒有一切組織形態。所以帝王中最厲害的李世民從孟子這受啟發,說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」!他們是好欺負,幾百年間誰都能欺負,但欺負到底,他們是要掀桌子的啊!
大丈夫生於世間,當以平天下為志向;如果想平定這亂世,當今天下,舍我孟軻其誰?
奔波三十載,54歲高齡的孟子依舊沒有心灰意冷,並且還有著捨我其誰的勇氣。當然我們上帝視角看,孟子無疑失敗了,但我們卻不能說孟子的理想破滅了,他依舊留下了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的治世理念。
並且這句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」,還在激勵著一個個後人;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而受宮刑,激勵他寫出《史記》的信念,是他覺得孔子以後500年就是他!
在這之後,華夏一有亂世,人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尋找明主。
諸葛孔明六出祁山,是將先主劉備視為明主;王猛辭桓溫而就苻堅,是覺得苻堅能平定天下;宗澤死前高呼過河!過河!岳飛風波亭高喊天日昭昭、天日昭昭,是痛恨自己未遇明主……
大略說來,夏啟家天下到商湯革命,470年而周朝建立;商湯立國到武王伐紂,又有550年;周公旦樹立周禮,到始皇帝一統華夏卻有整整800年;此後兩漢四百多年,再有魏晉南北朝大分裂;及至隋唐長期統一,已經漢末近五百年矣……
中國歷史上特有的周期規律呈現而來;幾百年大治理,就要有幾百年大分裂;這個500年的數字從孟子提出起就不精準,但趨勢卻從未改變;後來人們將這個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勢,稱為歷史周期論。
那麼這種規律背後的根源是什麼呢?四個字土地兼并!亂世之後人丁稀少,每個人都有足夠耕地,自然都是其樂融融;數百年間人口增長,加上土地兼并,沒了土地的人越來越多;當餓殍遍地之時,就是大亂之始。
但這一平一亂之間,就是上千萬人口的消逝,數百萬家庭的離散,其中多少悲傷有誰可知?
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這種重複發生的悲劇,孟子說了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,他說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這話不全是為平民說的啊!
平民看似最好欺負,但一切社稷、尊貴都是建立在無數平民基礎上的,沒有人就沒有一切組織形態。所以帝王中最厲害的李世民從孟子這受啟發,說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」!他們是好欺負,幾百年間誰都能欺負,但欺負到底,他們是要掀桌子的啊!
 呂純弘 • 2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6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9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