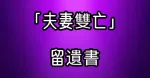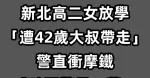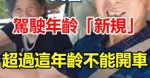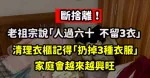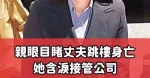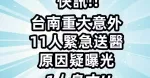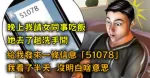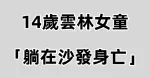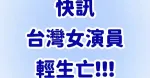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孟子發現一個規律:華夏每500年必然復興,2000年來已成現實!

3/3
所以一定程度上說,孟子比孔子更偉大,孔子的克己復禮是追求短時間的秩序修訂,是治標不治本,孔子是想再恢復幾百年安定。
而孟子的「民貴君輕」、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,是講你好了、別人也要還好,才能互相其樂融融。老子也說過「天之道,損有餘而補不足」,自然規律是損多餘的來補充不足的;老子還說「人之道,損不足以奉有餘」,但人卻總是要本就缺少的來侍奉有盈餘的;到最後人不能走出周期,總是等到自然規律再來一次次調整!
明朝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楊慎,23歲狀元及第;卻因觸怒嘉靖皇帝,流放雲南三十年;老死不得歸鄉,大徹大悟而成「明朝三大才子之首」,這裡引他一首《西江月》:
道德三皇五帝,功名夏後商周。七雄五霸斗春秋。頃刻興亡過手。青史幾行名姓,北邙無數荒丘。前人田地後人收。說甚龍爭虎鬥。
小到一個人的生老病死,再到一個家族的興衰過往,大到王朝循環更替,道理再清晰不過。但從孟子開始,人們卻反覆在同一個坑裡跌倒無數次,根結何在——克服人性,讓理性戰勝獸性!
什麼時候,李世民的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」,不再只是一句漂亮話;不再有出身貧農,看完孟子的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就把人家排位趕出孔廟的朱元璋;真正做到民貴君輕,人們也就戰勝自己,不再需要天道來損有餘而補不足了啊!
一次次循環往復,在這幾千個春華秋實的輪替中,留下的是累計上千萬家庭的離散,數千萬血淚的經驗教訓。從齊宣王到沒有人再稱王了,這天道一直在等著土地上的人,行「真王道」、推「真仁政」,那時人也就超越了天道的輪迴,真叫做欲與天公試比高啊!
而孟子的「民貴君輕」、「仁政」、「王道」,是講你好了、別人也要還好,才能互相其樂融融。老子也說過「天之道,損有餘而補不足」,自然規律是損多餘的來補充不足的;老子還說「人之道,損不足以奉有餘」,但人卻總是要本就缺少的來侍奉有盈餘的;到最後人不能走出周期,總是等到自然規律再來一次次調整!
明朝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楊慎,23歲狀元及第;卻因觸怒嘉靖皇帝,流放雲南三十年;老死不得歸鄉,大徹大悟而成「明朝三大才子之首」,這裡引他一首《西江月》:
道德三皇五帝,功名夏後商周。七雄五霸斗春秋。頃刻興亡過手。青史幾行名姓,北邙無數荒丘。前人田地後人收。說甚龍爭虎鬥。
小到一個人的生老病死,再到一個家族的興衰過往,大到王朝循環更替,道理再清晰不過。但從孟子開始,人們卻反覆在同一個坑裡跌倒無數次,根結何在——克服人性,讓理性戰勝獸性!
什麼時候,李世民的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」,不再只是一句漂亮話;不再有出身貧農,看完孟子的「民為貴,社稷次之,君為輕」,就把人家排位趕出孔廟的朱元璋;真正做到民貴君輕,人們也就戰勝自己,不再需要天道來損有餘而補不足了啊!
一次次循環往復,在這幾千個春華秋實的輪替中,留下的是累計上千萬家庭的離散,數千萬血淚的經驗教訓。從齊宣王到沒有人再稱王了,這天道一直在等著土地上的人,行「真王道」、推「真仁政」,那時人也就超越了天道的輪迴,真叫做欲與天公試比高啊!
 呂純弘 • 3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6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9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3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